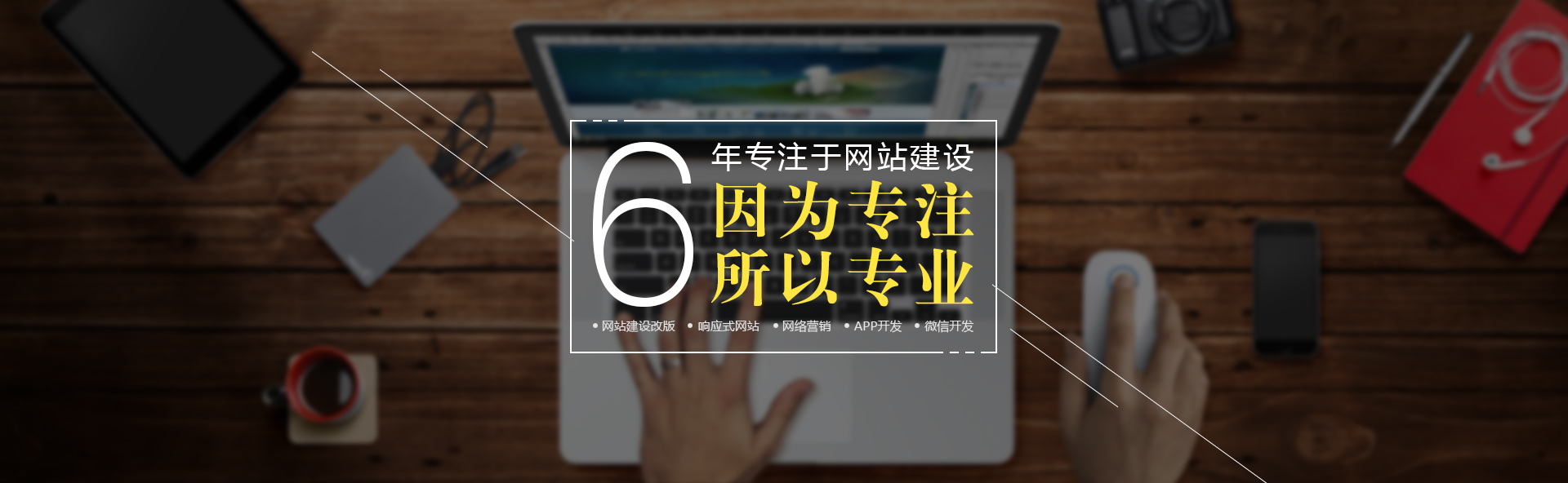在巴塔哥尼亚天际线上,这座山峰令人过目不忘。无论从任何一个方向看去,它都像一把覆盖着冰霜的利刃,直插云霄。凌厉而高耸的线条使它得到了一个简单而粗暴的名字——“塔”。这便是托雷峰(Cerro Torre)。初见没人知道人类第一次将目光投向托雷峰的确切时间。早在西班牙殖民者占领这里前约1万年,当地的原住民特尔维切人便已经在如今托雷峰所处的查尔腾一带生活。15世纪西班牙殖民者的入侵导致了特尔维切人的灭绝。已知的第一个见证了查尔腾山域的西方人,是1782年的西班牙人Antonio de Viedma,他在日记中这样形容那座在群山中分外显眼的山峰:“una torre”,一座塔。但在随后的一个多世纪里,没有人曾尝试攀登甚至接近这片山域。直到1915年,一支由瑞士人Alfred Kölliker带领的探险队才第一次探索了这里,对其周边地区绘制了地图,并在周围的小山峰上尝试了一些简单的攀登。▲Chaltén Massif,左起第一座为托雷峰。回国后,他们将掌握的信息成书并出版,虽然那是一个信息流通并不快速的时代,但这些信息仍然在南美和欧洲的登山群体中引起了不少关注。1930s始,对于该地区山峰的攀登尝试和首登竞争逐渐兴起。作为查尔腾山域最具标志性的山峰,菲茨罗伊峰于1952年2月2日被Lionel Terray和Gudio Magnone首次登顶。在顶峰与仍是处女地的托雷峰相望后,Terray和Magnone在日后的宣讲中将其描述为“不可能攀登的山”。但越是这样的说辞,便越是唤起登山家们竞相尝试的渴望。Cesare Maestri切萨雷·马埃斯特里,如果按意大利语的发音,他的名字应是这样翻译。说起托雷峰的首登之谜,Cesare Maestri是绝对无法回避的争议人物。▲年轻的Maestri。在他的家乡意大利特伦蒂诺,Maestri是一个以意志和技术赢得了不小威望的登山者,他在多洛美地的一系列无保护攀登使他成为了当地报纸上的常客。1954年,意大利决定派出探险队攀登K2,他却被拒绝在名单之外。但一封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信将托雷峰写入了Maestri的脑海,信中写道:“来这里吧,你会找到那座配得上你声名的山。”寄信人名为Cesarino Fava,一名来自Maestri的家乡附近村落的攀登者,二战之后,Fava移民到了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他看到Maestri为了向意大利登山队证明自己而连穿多洛美地诸峰的新闻后,向Maestri发出了那封邀请信。不过这时,他们还并不认识。▲Cesarino Fava1957年末,Maestri跟随一只意大利探险队出发,来到了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并于1958年初到达了托雷峰地区。但这次尝试以失败告终:在山的西面,来自意大利的另一支队伍,Bonatti和Mauri被山上狂暴的天气和艰险的地形逼下了山;而Maestri所在的队伍则更加简单直接,禁止队员去尝试攀登。不过Maestri并没有白跑一趟,他已经在脑海中构想了一条可能的攀登路线。而且显然他并不想多等,1958年12月21日,在Fava的帮助下,Maestri和奥地利攀冰好手Toni Egger搭档,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与Fava汇合后,便前往了托雷峰。Maestri计划从山的东壁根部攀登至征服坳(Col of Conquest)—— 一个位于托雷峰北壁的山坳,然后横切至北壁一路到达顶峰。▲托雷峰的部分线路汇总,2005年由Rolando Garibotti完成。图片右侧相连处的山坳为征服坳在攀登开始的一两个星期里,Toni因为脚部受伤一直坐在营地里。在Fava的帮助下,Maestri用四天的时间向征服坳的方向攀登了近1000英尺(约330米),并沿路固定路绳。但当天气使他们不得不撤回大本营时,从路绳的最高点到顶峰,仍然有3000英尺(约910米)的垂直路段。狂风几个星期里一直不停的席卷着这片山域,几人在大本营中谈天说地,关于家乡、战争和攀登。当狂风最终退去,Toni的脚伤也已经恢复,攀登立即开始。1959年1月28日,他们从冰川顶部的雪洞营地出发,开始向顶峰推进。Maestri和Toni凭借精湛的技术在前方领攀,Fava便在后面负责拖拽物资,仅仅用时一天,三人便沿着路绳来到了征服坳下方的三角雪原。但从这里再向上,便没有了路绳,Fava深知自己的能力不足会影响队伍的速度和物资消耗,便决定下撤至雪洞等待两人的凯旋。从这里开始,Maestri和Toni以惊人的速度向顶峰攀登,Toni出色且大胆的攀冰方式让队伍进展迅速,他们在岩壁上留下了30余个挂片(当时使用的是凿入岩壁的铁钉,尾部有一个环形铁片用于悬挂绳索或装备),多数是用来保护和绳降的锚点。1959年1月31日,他们站在了托雷峰的顶峰。▲托雷峰顶峰。下降的过程中,风力逐渐加大,云雾开始蔓延在托雷峰的四周,小型的雪崩不断的从顶峰的冰蘑菇上脱落。并且不知为何,他们并没有使用攀登时已经做好的锚点下降,这使得二人连续两晚在肆虐的坏天气中无遮无拦的露宿。当下撤至距离固定路绳仅有几十米处时,一声“死亡口哨”响彻山间,一堵白墙从上方压面而来。Maestri本能的贴紧墙壁,并紧紧攥住手中的绳子以拉住Toni。但当一切尘埃落定,绳的另一端除了山间咆哮的风,没留下任何重量。2月3日,留守大本营的Fava仍然没有等到凯旋归来的队友,他一次次地走出雪洞向上张望,什么都没有。在经过过去3天狂风的肆虐后,他决定下撤去寻求帮助。当他走出雪洞最后一次向上看去找寻自己的朋友时,他看到雪地中有一个黑点。他冲到那个黑点面前,Maestri艰难地从雪地中抬起头,勉强的用声音重复着:“Toni,Toni,Toni…"回到意大利后,Maestri宣布他和他的搭档Toni成功登顶了托雷峰,但Toni在下撤过程中不幸遭遇雪崩遇难,唯一存有能证明登顶的照片的相机随着Toni一起消失在冰雪之中。▲Maestri凯旋归来。在那个攀登者的说辞很少被质疑的年代,他的凯旋受到了莫大的追捧,粉丝、家人、记者、摄影师。即便是Lionel Terray,完成了1952年菲茨罗伊峰首攀的人,也盛赞其为“史上最伟大的攀登”。Maestri是个英雄,至少,目前是的。疑云骤起虽然在那个年代,人们总是倾向于相信登山者的陈述,但对于无凭无据的空口之辞,质疑声音仍然会在某个角落滋生。而对于Maestri首次公开的质疑,出自几个英国人之口。1966年,阿尔法俱乐部的晚餐上,一个叫Mick Burke的人问他的朋友们是否愿意加入一支去往南美的探险队。讨论攀登的目标时,有人提出托雷峰,迷迷糊糊中,这群醉汉认为这是个好想法。于是经过一年的筹划,1967年的12月初,团队抵达了坐落在一段狭长的、生长着树木的山谷中的大本营。▲Dougal Haston, Martin Boysen, Mick Burke, Peter Crew.在欧美的攀登文化中,线路的创新性和技术难度是体现一个、或一组攀登者能力的重要因素。出于不愿重复前人的脚步的想法,一行人制定了一条新路线:东南山脊路线——易于接近,岩壁路段更多。接下来的两周,整个团队都在向山脚运输物资。虽然天气从来没有缓和过,但在巴塔哥尼亚,天气说变就变,必须随时做好向上攀登的准备,在难得的几个天气窗口期中,Boysen、Haston和Burke尽力地将路从山脚下修到山坳上。不过更多的情况下,几人刚刚接近山脚下,天气就开始变差,迫使团队回到营地中。整个12月中,没有一天的时间适宜团队向上攀登。12月27日,天空突然放晴。一行人迅速动身向上攀登,当晚,所有人都到达了冰川顶部的雪洞营地。一转眼,天色变差,所有人又下撤至大本营。然而第二天,又是万里无云。▲图中路线所在便是东南山脊。图片来源:PATAclimb.com终于在一天下午,他们抵达了“耐心山坳”(Col de la Pasiencia)。当攀登报告写到这里,Peter Crew已经放弃了对时间的陈述,只知道在过去的日子里,队伍在山上被天气追赶着上上下下。但到达山坳也仅仅是攀登线路的三分之一,山坳之上,还有900多米的近乎垂直的岩壁路线在等待着他们。而在岩壁上攀登的进度是缓慢的,在危险而骇人的花岗岩壁上,队伍一天只能向上推进大约两到三个绳距,不到一百米,何况能维持一整天好天气的日子,屈指可数。“耐心山坳”上方450米处,在一面光滑且没有裂缝可以设置保护点的岩壁前,领攀的三人花费了7个小时,却始终无法攻克,他们需要岩钉,否则便无法前进。当他们撤回山坳,准备从下方的营地补充岩钉的时候,坏天气再次袭来。游戏结束,他们的最高点在“耐心山坳”上方450米的位置,距离顶峰还有另外三分之一的路程。▲1968年的东南山脊线路,图中标出了他们到达的最高点。图片来源:PATAclimb.com这次(1968年)攀登队伍集结的是当时世界上最为顶尖的攀登者,选择的路线相比Maestri的路线容易,但却与Maestri宣称三天半到顶的进度相去甚远。在三个月的周期中,他们断断续续向上推进了10余天,却只达到了三分之二的高度。并且截至68年队伍的最高点,他们没有在岩壁中打入任何一个挂片,而Maestri宣称他们在攀登过程中手工打入了30多个挂片,平均每一个需要敲击500多次。仅仅是完成这项工作,就要花费他们近20个小时,而他们在征服坳之上一共才呆了2天,这样的攀登速度快到令人匪夷所思。疑问浮出水面,Maestri的故事也许太过美好了?空气压缩机质疑声愈演愈烈,Maestri被激怒了,他决定返回托雷峰,他要证明自己能够登顶。1970年5月(南半球的冬季),他重新召集了好友Fava,组建了一支队伍,带着阿特拉斯设备公司赞助的一台内燃空气压缩机和电钻、绞盘和燃料等数千磅重的装备,重新来到了托雷峰的山脚下。冰的季节性和不稳定性让挂片无法派上用场,挂片只能打在稳定的岩石中,而1959年的东壁转北壁路线在登顶前需要连续翻越巨大的冰蘑菇,所以这一次,Maestri选择了1968队伍的攀登路线——东南山脊路线。在攀登的前期,Maestri只是零散地在保护站的位置上打了一些挂片,直到抵达1968年队伍所描述的困难地段之前,Maestri都在以这样的方式推进着。▲2005年Garibotti攀登北壁线路图片。但从那片空空如也的岩壁开始,Maestri发动了压缩机,开始以2秒一个的速度疯狂地将挂片打入岩壁,将绳索和绳梯挂进挂片,踩在绳梯上打入下一个挂片……“Cesare,住手!”Fava朝着上方大声喊叫,但Maestri全然不顾。在向右横切了90米,打入了约100个挂片之后,他们抵达了一个相对平坦的地方。头顶上距离顶峰还有300多米,他们选择了撤退,冬季尝试结束,耗时45天。几个月后的12月,Maestri再次动身前往托雷峰,准备完成最后300米。Fava选择了退出,Maestri不得不组建新的队伍,但这并没有影响他再次启动那台压缩机。▲图中用圆圈圈中的便是1970年Maestri打入的挂片。摄影:Dorte Pietron后面的故事,便尽人皆知了。在线路上打入了近400个挂片后,Maestri宣布成功登顶,并将那台压缩机挂在了顶峰下方60米的位置,且至今仍悬挂在那里,线路由此得名:压缩机线路(The Compressor Route)。▲1970年悬挂至今的压缩机。但就在世人觉得托雷峰的首登之争就此结束时,Maestri再次给了登山界一记重拳。不,他没有登顶1974年,另一支队伍的发现给本就迷雾重重的真相再添一笔。1974年11月,一组美国登山者,John Bragg和Jim Donini搭着邮差的车来到了巴塔哥尼亚地区,在这里偶然遇到了两个熟人,同为美国人的攀登者Brian和Ben。两组人马很快达成共识,并来到了托雷峰脚下。▲Jim Donini一如往常,巴塔哥尼亚用他特有的方式欢迎了这队攀登者。从他们到达大本营开始,狂风和降雪便不断的侵袭着,直到圣诞节,大家才开始从帐篷里走出来。12月26日,Bragg尝试附近的一座山峰未果回到营地,突然间一个人跑进来冲Bragg说到:“你TM不会相信我们找到了什么!”当天早些时候,一行人在托雷冰川向山脚接近的途中,看到一只狐狸在啃食什么东西。那是一条小腿,人的小腿。脚上还套着一只靴子,制造于奥地利基茨比厄尔。那是Toni Egger的遗体,一部分遗体。▲1974年美国队发现的Toni Egger部分遗骸。从现场的状况来判断,Maestri关于Toni之死的说法是真实的,遗体周围大量的石块确实符合雪崩致死的特点。但同时,几人试图在遗体的周围寻找传说中的相机,一无所获。他们将Toni的遗骸集中起来,埋葬在了石块之下。并带走了一些器械,作为证据带往了欧洲。这个发现,让Bragg和Donini产生了攀登托雷峰旁边的艾格塔峰(Torre Egger)的想法。1975年12月,Bragg和Donini以及另一个队员Jay Wilson回到了查尔腾,准备攀登艾格塔峰。他们计划沿着Maestri和Egger的攀登线路,从托雷峰的东壁出发,在托雷峰和艾格塔峰之间的“征服坳”与其攀登路线分离,右行攀登艾格塔峰的南壁。▲左边标注为托雷峰,右边标注为艾格塔峰,图中标注了三角雪原和征服坳的位置。当他们从线路起点开始攀登,很快,历史的痕迹接二连三的出现在眼前。“It was like a trip through history."(那像是一次穿行于历史的攀登),Donini在一次采访中这样说道。1959年那次攀登中所使用的器械都仍然留在原位:木楔、岩钉、挂在主锁里已经腐烂的绳索……攀登的技术难度非常高,一切正如Maestri所描述的那样。东壁转北壁路线自从1959年之后再也没有人尝试过,Donini和Bragg是继1959年之后尝试这段线路的第一队人马。▲1959年留在石缝中的木楔。当他们推进到征服坳下方的墙壁中间时,在三角雪原的下方,他们发现了一个由Maestri等人留下的废弃装备堆,距离线路起点约1000英尺(约330米)的地方。而在到达这个装备废弃堆之前的一个绳距则表现的非常怪异:在整段绳距上,所有的装备都被放置的非常接近,每不到一米便有一个,而且几乎在每一个主锁上,绳子都被打了一个双套结(双套结一般用于将自己固定在保护站上),没人能解释清楚原因。而后,队伍越过装备废弃堆继续向上攀登,再也没有出现任何的装备、甚至放置装备的痕迹。而且线路的难度也与Maestri描述的情况完全不同。从装备堆向上,Maestri描述其“非常简单”,实际上却比看上去要难得多;而横切至征服坳的绳距,Maestri则宣称非常困难,实则存在一个很宽的岩架,从下方角度看去无法被发现,那是从线路开始到征服坳的所有地形中最简单的一段。▲从艾格塔峰向下看去,很容易发现那个岩架,但只能被高于它的视角看见,从下方望去是无法看见的。极有可能,Maestri不仅没有在1959年登顶托雷峰,他甚至都没能到达征服坳。“I think his high point is the goddamned equipment dump, only a thousand feet up."(我认为他的最高点就是那个该死的装备堆,1000英尺高而已。)Donini说。此外,1971年,Maestri还给了整个登山界一个响亮的耳光:他并没有在1970年的尝试中登顶托雷锋,而是只到达了岩壁的顶端。原因是他认为顶端的冰蘑菇和积雪不是山的一部分,早晚有一天会被吹下去。若1970年Maestri真的没有完成压缩机线路,而1959年的首登又如此疑点重重,也许托雷峰的顶峰,还没有人类涉足过。不过很快,那里便将迎来一批访客。莱科的蜘蛛托雷峰首次无可争议的登顶,是于1974年由另一支意大利队伍完成的。▲Casimiro FerrariCasimiro Ferrari——1970年另一支攀登托雷峰失败的、由Carlo Mauri带领的队伍中的一员。自从见到托雷峰,那里便成了他魂牵梦萦之地。于是1973年11月17日,他带领着名为“Ragni di Lecco”(莱科的蜘蛛)的登山探险队驶离了意大利。▲Ragni di Lecco队伍合照。现在看来,Ferrari和他的攀登搭档Mario Conti真正找到了托雷峰的弱点:他们计划沿着1970年失败的脚步,攀登其冰雪覆盖的西壁。12月24日,团队开始向西南山脊下方的山坳——希望坳(Col of Hope)攀登,12月26日傍晚,他们已经抵达了希望坳之上约400米的地方。但食物储备的持续消耗已经不足以支撑整个团队向上,他们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将团队人数缩减至4人。1月6日,4人抓住短暂的好天气开始向上攀登。在顶峰的冰蘑菇下方再次遇到恶劣天气,被迫在雪洞里等待了一周。1974年1月13日傍晚5点45分,Daniele Chiappa,Mario Conti,Casimiro Ferrari和Pino Negri站在了托雷峰的顶点。历史上第一次无可争议的登顶了托雷峰,并将这条登顶线路命名为“Ragni”(600m, 90°, M4)。▲2013年由Paul McSorley拍摄于Ragni路线最后一个冰蘑菇。▲Ragni 线路。图片来源:PATAclimb.com至此,攀登托雷峰的两条主要线路已经开辟。从1974年至今,无论哪一位登山者,开辟了什么样的新线路,最终都会在登顶前汇聚到这两条线路的其中一条里。不过在压缩机路线上,还留下了一个小问题。Maestri并没有登顶,他仅仅是将挂片打到了顶峰之下,压缩机路线还没有被完成过。1978年12月,Jim Bridwell和他的两个搭档来到巴塔哥尼亚,准备攀登托雷峰。但当他的两名搭档看到托雷峰的那一刻,他们摇了摇头便转身回家了。Bridwell是优胜美地攀岩的风云人物,在大岩壁攀登的黄金时代过后,Birdwell成为了下一代优胜美地攀岩人的首领,引领攀岩由器械攀登向自由攀登的革命。但同时,这群住在4号营地的流浪汉缩衣节食的过活,只为了攀岩。为了眼下这趟旅行,Bridwell计划了一年,也省吃俭用了一年,他当然不会就此放弃。▲Jim Bridwell圣诞前夜,他幸运的碰到了另一个美国攀登者,Steve Brewer。两人整合为一支新队伍,很快动身开始向山下进发,攀登9年前Maestri留下的“压缩机线路”。并且目标很明确,快速,轻装,独立,阿式攀登。12月26日,两人徒步抵达大本营。但也与之前任何尝试的队伍一样,被风雪挡在了大本营,不过很快,天气短暂的放晴,二人开始向山脚前进。但问题很快出现了,在遇见Brewer之前Bridwell曾在冰川的顶端挖了一个雪洞,并且把装备存在了里面。现在,经过多日的降雪,他们找不到那个雪洞了。上上下下了两次,他们都没有找到丢失的装备。无奈之下,他们撤出冰川并在这一区域寻找其他的攀登者,从他们手中收集了足够使用的装备,补充了一些食物之后,返回了托雷峰。1979年1月3日凌晨3:30,他们开始攀登。Bridwell和优胜美地的新一代攀岩者们以速度著称:酋长岩900米高的“鼻子”路线,首攀用了16个月,第二组人马重复用了一周。而Bridwell只带了两个人,仅用了一天。▲Bridwell和他在优胜美地的同伴们。在托雷峰的攀登中,他也延续了这一作风,当日凌晨5:30,他们便抵达了“耐心山坳”。攀过Maestri留下的“挂片横切”(Bolt Traverse)段,是一段烟囱(背靠墙脚踩对面墙攀爬的裂缝),又是一连串挂片,又是一段烟囱…午夜,他们在顶部斗壁下方不远的地方设置好了露营,简单吃过东西之后,在呼啸的风中捱过一夜。第二天,再次经过一段冰岩混合的地形之后,他们来到了顶部的斗壁下,两人开始同步攀登(两人一前一后同时攀登,领攀者放置保护点,跟攀者回收保护点,更高效但更危险)。虽然Jim和它的朋友们在优胜美地掀起了自由攀登革命,但在托雷峰,在这样一个危险的极端环境下,Jim还是选择了保守的器械攀登。“这是我曾攀登过的最危险的地方。”1979年1月4日,Bridwell和Brewer站在了托雷峰的顶峰,第一次真正完成了“压缩机路线”(800m, 7a, C2, WI5)。虽然,用的是一种不太体面的方法。▲Jim Bridwell 在托雷峰顶,身后是伟岸的菲茨罗伊峰。此后,还有很多的阿式攀登精英或团队尝试过攀登托雷峰。1985年7月8日,来自意大利的Paolo Caruso,Maurizio Giarolli 和 Ermanno Salvaterra 沿“压缩机路线”完成了托雷峰的首次冬攀。1985年11月26日,瑞士人Marco Pedrini沿压缩机路线完成了首次独攀。2004年,一支来自意大利的三人队伍开辟了东壁直上线路“Quinque Anni ad Paradisum”(900m 90˚ 6c A4)。2012年1月16日,美国人Hayden Kennedy和加拿大人Jason Kruk搭档,第一次“干净利落”(fair mean)地完成了东南山脊路线,没有使用任何一个Maestri打入的挂片,并且在下降的过程中撬掉了近400个挂片中的125个。这一举动在登山界引起了巨大的争论,有人认为他们破坏了历史,有人认为他们恢复了山峰原本的面貌。“我其实只是想给予这座山峰应有的尊重。”Hayden说。由于这些挂片降低了托雷峰的攀登难度,“压缩机线路”吸引了一些颇有能力但并不属于精英级别的登山者前来尝试,这带动了查尔腾小镇的经济发展,而撬掉挂片对此无疑是一记重击。▲Hayden Kennedy 和 Jason Kruk,其中Hayden Kennedy已于2017年10月7日因女友雪崩遇难而自杀身亡。但山峰西侧的Ragni路线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2013年2月,Markus Pucher沿Ragni路线完成了首次无保护攀登;2015年2月,Marc-André Leclerc仅用一天完成了托雷峰有史以来最高难度的独攀:“Corkscrew”线路(5.10d,A1)。时过境迁,首登之谜貌似已经被渐渐淡忘,托雷峰上不断有人刷新着历史。但2003年,一件证据的出现,让本已平息的首登疑云,波澜再起。最后一块拼图2003年,Toni的另一只腿骨和一部分脊椎残骸出现在冰川上,其腿上附着的皮肉组织仍完好如初。但发现这部分残骸的地点显得有些奇怪。在《The Tower》一书中,作者Kelly Cordes对图片的背景地标进行了对比分析后发现,1974年的遗骸发现位置位于托雷冰川的上部和主体交汇的地方,距离托雷峰直线距离1.1英里(约1770米),高低落差700米。2003年的位置仅在1974年地点的下方100米处。▲1974年遗体被发现的位置位于右下角的红圈内。图片来源:PATAclimb.com从1959年到1974年,15年间,遗体随冰川移动了近1.8千米。然而,从1974年到2003年的近30年间,却仅移动了约100米?诚然,根据冰川的地形和类型不同,在同一条冰川的不同位置,移动速度也可能有剧烈变化。但是这个令人诧异的数字,还是让人不免感到奇怪。另外,根据现场的图片,Toni腰间的绳索的绑缚方式也不像Maestri所描述,处于一个绳降的状态中。重重疑点,使得1959年的首登传奇变得扑朔迷离:超现实的攀登速度、废弃的装备堆、奇怪的遗体发现地点、与陈述不符的绳结…没有答案的谜题越来越多,直到Rolando Garibotti的出现。▲Rolando GaribottiRolando是个活着的传奇,他出生于意大利,但童年是在阿根廷的巴塔哥尼亚北部度过的。15岁时他便开始在查尔腾山域进行技术性攀登,17岁时便和一个高中同学攀登压缩机线路,并且到达了离顶峰仅仅不到5个绳距的地方。2005年11月,Rolando在托雷峰完成了一次史无前例的攀登,他与Salvaterra和Beltrami沿着1959年Maestri和Egger的东壁转北壁攀登路线成功登顶托雷峰,线路命名为El Arca de los Vientos(550m, 60˚, 6b+, C1),并且因此提名了攀登界的最高奖项——Piolet d'Or(金冰镐奖)。▲托雷峰的北壁,线路11标注了Garibotti等人的攀登线路El Arca,也是原1959年Maestri-Egger线路。2004年,Rolando曾在美国登山年鉴(American Alpine Journal,以下简称AAJ)发表了一篇长达18页的文章,研究并总结了多支队伍的托雷峰攀登报告,详尽论证了Maestri的登顶表述与实际情况中的矛盾之处。这篇文章引起了时任AAJ编辑的Kelly Cordes的注意,这促成了《The Tower》一书的写作和出版,也为击破Maestri的故事添加了最重要的一块拼图。2013年,Rolando和Salvaterra在编写一本新书的过程中注意到了一张出自Maestri之手的照片。这张照片出现在Maestri的自传《攀登是我的职业》中,Maestri宣称这是一张记录Toni正在攀登托雷峰底部一段俯角地形的照片。▲书中描述的图片。图片来源:Alpinist.comRolando的攀登经验告诉他,这很明显不是托雷峰底部的地形。但照片的剪裁方式,让他无法辨认照片具体的实际拍摄地点。大约一年后,Kelly找到Rolando,希望他认真的辨认一下照片的拍摄地点,Rolando用了很长时间研究山谷地形的照片后,终于确定了照片拍摄的位置。那是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在托雷峰山脊线的北端,一个叫Perfil de Indio的小山尖,向南方的山坳拍摄。▲Col Sdandhardt的图片。拍摄者位于中间偏右的小山尖上,被拍摄者位于其左下方的小山坳处。如此,若假设Toni的遇难地点也在这个位置,其遗体发现的地点也就显得更合理一些。这张照片成为了击碎Maestri弥天谎言的一记重击,而2015年《The Tower》一书的出版则几乎可以说是一剑封喉。如今,仍然有一些人坚持认为Maestri在1959年成功登顶,这几乎成为了一种宗教信仰。但在国际登山界,更广泛的观点还是认为Maestri没有成功登顶托雷峰,他们的最高点,仅仅是三角冰原下的那堆废弃装备。2021年1月19日,Maestri带着真相与世长辞,世人终究没能等到他将事实和盘托出。有人认为他是个夸夸其谈的骗子,有人认为他是成就伟大的英雄。种种证据表明,他确实没有登顶,但无论多少证据,那终是世人的推测。人们只能根据一件件证据拼凑出一幅模糊不清的图景,而至于真相究竟如何,他为什么对真相闭口不谈,随着Maestri的离世,我们将永远无法得知。只有托雷峰,依然沉默的耸立在那里。但对于一些纯粹的攀登者来说,给予一座山最崇高的尊重,不仅仅是还原真相。David Lama,天才攀岩者2009年,一个来自奥地利的毛头小子宣称,他要用自由攀的方式,完成著名的压缩机线路。他叫David Lama,是攀岩界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David出生于1990年,母亲是奥地利人,父亲是尼泊尔的高山向导。宣布自由攀登托雷峰这一年,他年仅19岁。▲David Lama这一宣布并不是空穴来风,David Lama极具攀登天赋,他从小开始攀岩,并在IFSC的世界杯赛场上屡屡夺冠,是攀登界的天才少年。但这时,他也只是在聚光灯照耀的竞技场上、山野市郊的岩场中有着过人天赋的攀岩者。但托雷峰可不是下车走上十几分钟就可以晒着太阳喝着咖啡的岩场。自由攀爬(Free Climbing),也就是只凭借自己的手脚和冰雪器械攀爬冰面和岩石的天然结构,绳索和技术装备仅作为跌落的保护措施。相比前人所使用的器械攀登,自由攀登无疑是一种难度更大,更加纯粹的方式。虽然从1958年起,托雷峰至今已经有过无数的团队,以各种方式,沿各种不同的线路尝试攀登。但通常队伍所采取的方式是自由攀登和器械攀登的混合,在简单的路段高效迅速地自由攀登,高难度路段使用钩挂装备和绳梯器械攀登。而面对平整无瑕的花岗岩壁,自由攀,很多人也许想都不敢想。▲Headwall直译为斗壁,地理学上一般解释为“悬崖上最高的一片墙壁”,在攀登中有“略带仰角的墙面”的意思但自由攀爬谈何容易。2009年11月,David便第一次进行了尝试,一层覆盖山体的冰霜将David挡在了“挂片横切”的面前,David不得不转头下山。2011年1月,比前一年仅高出10米的地方,因几乎一样的原因放弃。回到山下等待了个把星期后,他们再次迎来短暂的天气窗口。经历了连续两次的失败,David选择了不顾一切的登顶。一路上踩着挂片,拉着快挂,2月12日晚10点,他们终于成功登顶了托雷峰。▲David在顶峰抽拉连接着Peter的绳索。但这完全不是自由攀,完全不是。于是2012年1月,David第三次来到了托雷峰。与一年前同样的搭档,同样的红牛摄制组。很快,预报显示了一个合适的天气窗口,David和摄制组迅速制定了计划。1月19日,David和Peter出发了。由于几天前美国和加拿大的二人组合刚刚撬掉了顶部的125个挂片,David没有选择,他必须自由完攀。线路的难点,就是Maestri用连续的挂片通过的路段:“挂片横切”和“挂片梯子”(Bolt Ladder)。不足手指粗细的裂缝,半个指节都容不下的微小手点,无论是放置保护还是手抓脚踩,都给人以极度的不安全感,这两段平整的花岗岩壁是前进路上最大的阻碍。在压缩机线路原本的线路上,Maestri完全无视岩石的自然结构,在无法用手脚攀爬的地方打入挂片。所以为了完成自由攀,David必须另辟蹊径。▲David在攀登挂片横切段。在岩壁的根部,David坐在山脊上,换上柔软且富有摩擦力的攀岩鞋,粉袋系在腰间,安全带上连接着绳索,一边扣着不足一厘米宽的手点攀爬,一边在细细的裂缝中放置岩塞。抬起右腿向右下方的一个小斜面踩去,却发现无法借力,腿缩回来,却又发现其余的三点无法保持平衡。大叫一声,向后跌落,冲坠了6、7米之后,被绳索接住。此时他必须要回到起点,因为绳索已经为他提供了额外的力量,如果从跌落处继续攀登,便无法算作是自由攀。艰难的完成了挂片横切段后,太阳已然偏西。David和Peter在顶部斗壁下方不远的地方,选择了积雪与岩壁衔接之处,在雪地中挖出一块平台,拿出睡袋,准备迎接星辰升起。虽然第一天已经克服了“挂片横切”这道难关,但线路真正的难点在上方的斗壁上。那是到达顶峰之前的最后一片岩壁,这片岩壁无论是远看还是近看,都是如此的平整。表面的岩层很疏松,冰块也逐渐融化脱落,攀爬这片区域不能有任何闪失,否则后果非常严重。▲David在攀登顶部的斗壁。在摄像机的注视下,David沿着岩壁上的缝隙缓缓的从悬挂的压缩机旁经过。这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时刻,David Lama要还原托雷峰原本的面貌:它就是一座艰难的山峰,它就是一座只有少数天才才有机会触及巅峰的巨大挑战。8a/5.13b (后被降级为7c/5.12d),WI5,900米。这是David Lama给这条路线的定级。2012年1月21日,David Lama和Peter Ortner成功登顶。没有使用任何一个挂片,不论是Maestri的,还是自己携带的5个挂片。他们站在顶峰巨大的冰蘑菇上,望着千米之下的大地,无声胜有声。但就像Martin Boysen在红牛的影片中所说:“一代人认为‘啊一切都结束了’。但下一代的人们总会找到些新东西。”托雷峰仍伫立在地球的角落,静静等待着它的下一位访客。参考文献:「1」. 'The Tower: A Chronicle of Climbing and Controversy on Cerro Torre'. Kelly Cordes.「2」. 'The British Cerro Torre Expedition 1967/8'. Peter Crew「3」. 'A Mountain Unveiled: A Revealing Analysis of Cerro Torre's Tallest Tale.'. American Alpine Journal, 2004. Rolando Garibotti.「4」. 'Maestri Unbolted Update: Climber David Lama Frees Cerro Torre’s Compressor Route'. National Geographic, Feb 3rd 2012. Mary Anne Potts.「5」. 'Dozens of Bolts Added to Compressor Route'. Alpinist June 1st, 2010. Erik Lambert.「6」. 'Cerro Torre – The Lie and the Desecration'. Climbing, April 8 2009. Jim Donini.「7」. 'CERRO TORRE—THE ELEVENTH FAILURE'. American Alpine Club, 1973. Leo Dickinson.「8」. 'Completing the Puzzle: New Facts About the Claimed Ascent of Cerro Torre in 1959'. Alpinist, Feb 3rd 2015. Rolando Garibotti.「9」. 'CERRO TORRE — ALPINE STYLE'. American Alpine Club, 1980. Jim Bridwell.「10」. 'Cerro Torre and the 1985 first winter ascent'. Planet Mountan, June 23th 2015. Vinicio Stefanello.「11」.https://www.pataclimb.com/climbingareas/chalten/torregroup/torre.html「12」. 'Cerro Torre: A Snowball's Chance in Hell'. Redbull. David Lama, Peter Ortner.「13」. '谎言与诚信|登山史上最著名的登顶疑案'. 陶瓷虾
本文出自快速备案,转载时请注明出处及相应链接。